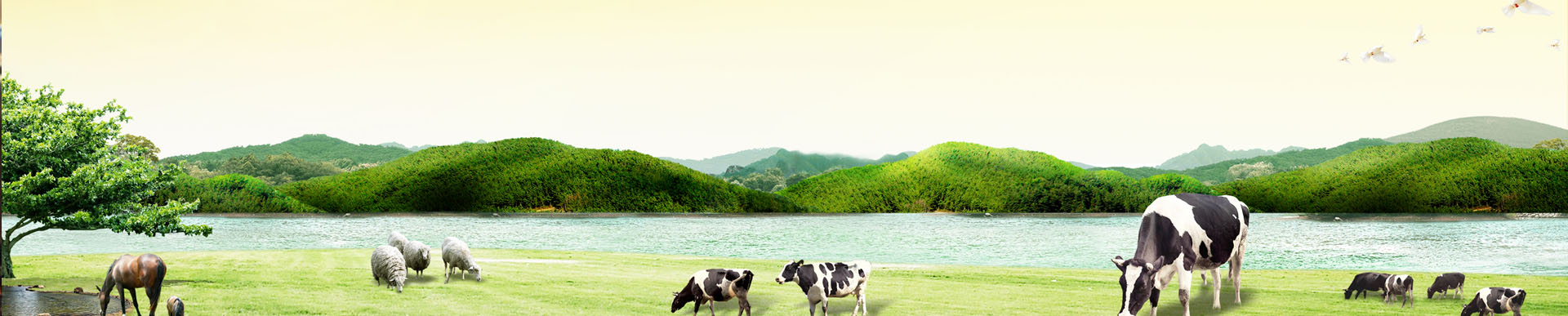畜牧業發展如何突圍“兩大困境”? ——訪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畜牧科學研究院院長蔣小松
“畜牧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更是民生保障產業。畜禽種業是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基礎和先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畜禽種業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良繁體系日趨完善。但種豬、白羽肉雞、優質種牛精液和胚胎等我國畜禽良種核心種源依賴進口的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明顯改觀。”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畜牧科學研究院院長蔣小松說,當前我國畜牧業發展主要面臨兩大困境,一是畜禽種業,二是養殖業用地。
蔣小松認為,我國缺乏完善的管理體系和政策措施,嚴重制約了畜禽種業的規范化發展。由于法規的缺位,相關研發者、生產者、經營者、使用者等從業群體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政府、研發機構和企業不能形成穩固的創新合力和發展動力,導致畜禽種業產業化水平提升和競爭實力提高進展十分緩慢。
同時,育種創新支撐薄弱,體制機制尚待完善。由于在育種科研組織模式、科技成果評價體系與轉移轉化機制上長期缺乏可操作性的統籌管理辦法,在國家財政對畜禽育種總體支持力度偏弱的情況下,科技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科研力量極其分散,研發內容不可避免地出現低水平重復,而協同創新使各方利益和成果難以有效得到保障,育種材料、共性技術成果不能有效交流共享,嚴重制約優異種質資源的保護和挖掘利用。
此外,我國對畜禽種業創新發展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體系還很不健全。目前,對畜禽育種創新人才激勵、金融服務、信息平臺建設等政策扶持上缺乏硬性規定和配套措施,難以激發創新活力,導致育種企業的基礎資源、技術儲備和創新人才等嚴重不足。同時,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知識產權確權、運用和保護力度還十分薄弱,嚴重制約畜禽育種的良性發展,育種企業實力總體不強。
如何突圍?蔣小松建議,國務院組織開展調查研究,盡快盡早出臺《畜禽種業促進條例》,明確畜禽育種發展的相關管理體制、總體目標、指導方針、發展規劃、功能定位、職責職能、投入保障、評價體系和監管措施等方面的內容。從國家層面進一步建立健全畜禽種業發展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促進我國畜禽育種的科學規范和可持續發展。
蔣小松說,通過規范管理和完善政策措施,提升畜禽種業地位,加快提高行業集中度和創新合力,形成自主創新體系,推動種業公司向育、繁、推一體化方向發展,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畜禽育種跨國領航企業集團和研發中心,搶占種業創新制高點,全面參與全球畜禽資源的配置,推進我國由畜產品生產和消費大國向畜禽種業強國邁進,盡早實現“中國畜禽”主要用“中國種”的目標。
“毋庸置疑,土地則是畜禽養殖和畜牧業發展的重要生產資料。但由于受養殖用地諸多條件的限制,嚴重影響了畜牧業的平穩健康發展。”蔣小松說,調查發現,當前養殖業用地主要存在三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首先,養殖用地保障難。雖然現行養殖用地政策允許使用一般性耕地,但受城市建設和工業用地擠壓,一般性耕地幾近不存在,養殖用地仍然一地難求。
其次,種養業用地人為割離。受現行基本農田不得用于建設養殖場限制,種植、養殖基地各在一邊,增加了種養結合難度和糞污資源化利用還田的成本,甚至造成環境污染隱患,威脅到農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最后,現行養殖用地政策不穩。養殖業主擔心隨時被關停或拆遷,不愿在基礎設施改善和設備升級方面再投入,阻礙了養殖新技術、新工藝的應用,導致疾病防控、疫情阻斷等生物安全防護能力難以系統性提高,畜牧業波動頻繁、波幅大,轉型升級步伐緩慢,難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養殖用地難題該如何破解?蔣小松建議,在國家層面建立基本養殖用地保障制度。
一是科學確定基本養殖用地規模。依據一定時期我國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對畜產品需求,有科學依據地確定基本養殖用地數量,以保障肉蛋奶等重要畜產品基本供給。基本養殖用地包括:農區畜禽養殖直接生產設施用地、牧區永久性放牧地(草原)及其關聯的必要輔助附屬設施用地等。
二是合理布局畜禽養殖場(基地)。根據環境容量和土地承載力,統籌考慮種植業、養殖業發展空間,合理進行畜禽養殖場(基地)的空間布局,以促進養殖業與種植業有機高效結合和農牧業綠色高質量發展。在基本農田區,按照“以地定畜、以畜肥地”的原則,科學配置集約高效基本養殖用地,實現畜禽糞肥就地就近低成本還田利用,以種帶養、以養促種。
三是建立基本養殖用地管理制度。基本養殖用地與基本農田在保障人民基本口糧與肉蛋奶等重要食品方面具同等重要作用,有必要參照永久基本農田管理模式建立系統化的基本養殖用地管理制度,采取行政、法律、經濟、技術等綜合手段,加強管理,以實現基本養殖用地的質量、數量、生態等全方面管護,并在法規層面保證基本養殖用地不得用作他用。
作者: 中國畜牧獸醫報記者 張林萍